
上周,发行商完美世界关闭了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Runic Games 开发商 火炬之光 和 滚刀 。为了纪念,我们请工作室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分享一些想法和轶事。
Runic 由 Travis Baldree 于 2008 年创立, 暗黑破坏神 共同创作者 Max Schaefer 和 Erich Schaefer、Peter Hu 以及已解散的 Flagship Studios 的成员,该工作室最著名的作品是 地狱之门:伦敦 和一个游戏叫 神话 那从未出现过。
尽管 Baldree 在 2014 年离开了 Runic,但他在那里的时光留下了很多想法和回忆。当我请他分享一些内容时,他写道:
我作为 Runic Games 的总裁负责运营,并且是首席工程师,我想你可以说是游戏总监。后 火炬之光2 发货,以及随后的错误开始(这就是叛逆银河的起源),一旦我们得到了最终成为的原型 HOB 总而言之,我离开了 Erich,开始了 Double Damage Games,并再次回到了微小的开发阶段。
我与 Runic 的故事到此结束,至少在专业意义上是这样 - 但团队继续发行 HOB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不过,这只是一条用来挂东西的线。我不想上一堂无聊的历史课,你也不想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找个时间把我逼到角落喝杯啤酒吧。
我只是想告诉您一些关于 Runic Games 的有趣的事情。我想与你分享一些粘糊糊的中心——什么 我 想要记住。
这一切都是通过我的经验过滤出来的,Runic 的任何其他人都可以给你提供一百个关于这个地方的其他轶事。如果你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希望你会问。
我想让你知道,在我们试图为自己确定未来六个月的同时,十六人团队如何愿意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坚持下去,而在旗舰关闭后,他们都可以分散到更安全的工作中。
我想告诉你关于原型 火炬之光 ,有一个来自 TurboSquid 的授权模型,看起来像一个双持耶稣,并且在他奔跑时顺便用两把剑刺伤了自己的脸。
我想转达我们第一个圣诞节的恐惧和轻松,当时西雅图的雪很深,公交车都在高中心,我们的银行账户是负数,我喝醉了,刷新着我们的富国银行账户页面,然后结束了,等待确保我们生存的电线接通,而符文的其余部分则庆祝并相信一切都会成功。
我们投了 火炬之光 (当时代号仍为 Delvers)到西雅图的 Big Fish Games。没有一个球场是不可能的!我得了重感冒,对 Sudafed 很着迷。他们的会议室布置得很奇怪,有一台台式投影仪,但附近没有电源插座,远处还有一面30度角的墙。我将笔记本电脑上的电缆拉到墙上高处的插座上,将电脑放在一些书本上保持平衡,同时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以倾斜的梯形投影。我几乎记不起球场上的任何事情——我确信那很糟糕。后来有人靠在桌子上说:“这一切都很棒,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 游戏。”
我们在 EA Redwood Shores 与 Frank Gibeau 坐在一起,唱歌跳舞,最后他说:“合同上的墨水下周就会干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窥视声。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参观完美世界在北京的旧办公室,漫步在艺术家和工程师的长桌之间,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缤纷的)遍布各处的动物主题加湿器,喷出蒸汽。铺着瓷砖的大浴室,窗户开着,很冷,每个人都在抽烟。
Zynga 突然联系了我们。他们一直在考虑租赁Flagship位于旧金山的旧办公空间,并看到了一段视频 神话 跑到那里。我们在宾·戈登(Bing Gordon)和其他一些人的旧办公室里会见了他们,他们坐在一张满是干擦涂鸦的桌子旁。我们谈论了他们的游戏,在某个时刻,Bing 靠在椅子上,伸出下巴,用每只手的前两个手指做出暗示性的摆动动作,说道:“现在,我要分开了。”和服”,并准备泄露他们的秘密。
我希望你能看到第一个技术原型 HOB - 我用了 风之杖 模型、动画和效果。我们让一个小林克在 Outset 岛上跑来跑去,推方块、扔石头、割草、游泳、攀爬墙壁,并通过等距摄像机大喊“哈!”,只是为了确保基本导航能够正常工作。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为工作室找到一个名字,在此期间我们被合并为“Surprise Truck”,这是 Max 投票选出的公司名称。由于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被使用,我接到源源不断的电话,询问“惊喜卡车运输”是否可以协助跨国搬家。
我们投了 火炬之光 到微软并有 广泛的 会议、公司审查,一切似乎进展顺利。令我们震惊的是,在艰难的过程结束后,他们决定让我们为他们制作一款《寓言》游戏。我们拒绝了。就在之前 火炬之光 发货后,一位微软代表在我们的第一次 PAX 上向我大喊:“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发布这个?”
我们非常接近成为 Turbine 的一员,并致力于制作霍比特人主题游戏。在我们第一次和他们共进晚餐时,我吃了最好的老式晚餐。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趣的是 一款手机游戏叫 武装英雄 窃取资产 火炬之光 ,当他们抗议时,我指出他们的文件名甚至有相同的拼写错误。
Max Schaefer 和我总是争论浮动伤害数字,所以有一天我为所有内容添加了浮动文本 - 包括脚步声。
......我想谈谈被烘烤的人为因素 进入 游戏。
我认为,特别是对于符文规模或更小的团队来说。我一直对制作游戏的人着迷,如果您也是如此,我建议您依偎在数字古物馆阅读吉米·马赫 (Jimmy Maher) 撰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章( 呜呜呜.FI LF Re.net )
如果你给 10 个不同的厨师一个食谱,他们都可以烘焙相同的东西,但你不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他们改变结果。游戏也是如此。建造它们的人会以令人惊讶且常常难以追踪的方式影响你所得到的东西的味道。这就是我喜欢游戏的部分原因——它们最终是一群人的非常人性化的表达,是秘密配方的产物,并且是经验丰富的 就这样 因为谁把东西扔进锅里。
在符文中确实如此。
Runic 是一家公司,我们的“文化部长”Wonder Russell 的狗最终在游戏中作为宠物,并拥有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 (法尔科!)
在这家公司,我们的原创科技艺术家 Adam Perin 确实可以像一把剑一样挥舞,配有小胡子十字护手和眼镜 - 以及一些精选的引言。
如果你玩过 火炬之光2 你可能会偶然发现首席关卡设计师帕特里克·布兰克 (Patrick Blank) 对七宝奇谋 (Goonies) 的喜爱程度。由于帕特里克在 Gearbox 的历史,哗众取宠在游戏后期秘密出现。
钓鱼和宠物都在 火炬之光 游戏因为 命运 这款游戏现在让我感觉自己老了,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小时候有人在父母的戴尔电脑上玩过这款游戏。
游戏是十亿个微小决策的总和,其中大多数决策从未被讨论过,这些决策以某种方式推动游戏。我可以查看 Runic 的输出,并看到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明确识别的数千种细微差别的个人表达。它几乎就像一本神秘的相册。
Jason Beck,我们最初的艺术总监,对棘手的开瓶器设计有着特殊的喜爱——你可以在第一个 Runic Games 标志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在他为之设计的一些界面和标志艺术作品中看到这一点。 命运 .
当我看到 Tim Swope 在他构建的图块集中的精确纹理图块时,我不可能错过它。
A 火炬之光 玩家提到他们患有一种名为“眼球震颤”的病症,这意味着相机抖动会使游戏基本上无法玩。 Marsh Lefler 添加了一个立即禁用它的选项。
我们的两位动画师科林和马特所运用的不同风格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凯尔·科尼利厄斯 (Kyle Cornelius) 的厚重物理概念得益于他的机械设计背景。 Mike Francina 大胆的造型、可爱的金属和宗教图像。
杰夫·米安诺夫斯基 (Jeff Mianowski) 华丽而复杂的人物衣柜。
马特·乌尔曼 (Matt Uelmen) 的乐谱将一切结合在一起。
这些因素对最终产品有直接影响——有很多因素更难以识别,但都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有所贡献。
在 Runic 存在的前六个月里,当我们试图确保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几乎成为了 PopCap 的一部分 - 以至于我们与 PopCap 的人们举办了一场认识聚会。那是在 2008 年,当时经济陷入困境,就在我们以为要去 PopCap 办公室与 John Vechey 和 Dave Roberts 握手达成交易的那天,它却夭折了。如果我说那天下午我的眼睛没有一点湿润,那我就是在撒谎。
但即使是追求这一目标的行为,我们在思考 PopCap 的潜在未来以及我们将如何实现发展时所做的精神转变, 坚持 在我们中。我认为你可以在我们制作的游戏中看到他们哲学的部分表达,试图让它们变得受欢迎、易于访问和可玩 任何地方 。我认为这是我们为《火炬之光》添加上网本模式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 - 上网本?那是什么?)
即使是 Runic 之外的人也产生了影响——在 PAX 上与粉丝进行的无数互动调整了我们制作游戏的轨迹,从无意中听到的评论,到直接讨论,再到推文和帖子。
Runic Games 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些优秀的人的特殊安排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即使,不知何故,我们最终都在同一个工作室,在相同的配置中,在未来的某个日期。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些游戏的风味永远、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这其中有一种忧郁。
但...
我还知道,这些出色的人将在他们下一步所做的任何事情中添加他们自己的指纹,当我看到它时,我会认出它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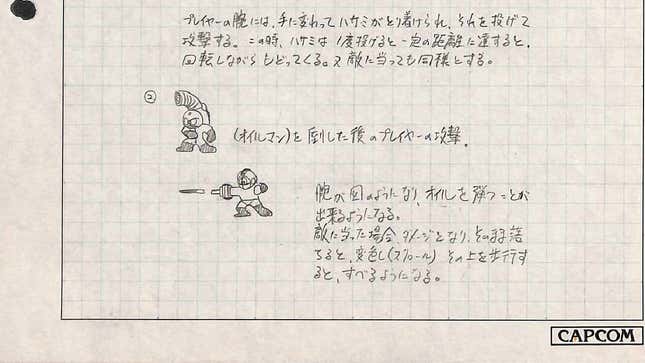









留言